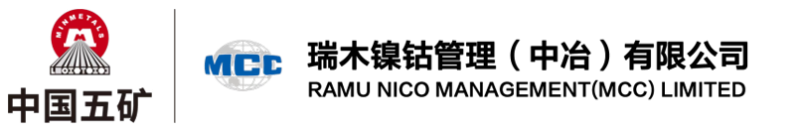矿山的雨,有很多样子。
雨有时会不分昼夜地袭来。淅淅沥沥,似没有尽头。丝丝落下,如同一张轻柔的网,罩住整片矿区。抬眼望去,沉沉的淡乌色云占据整片天空,偌大一片天,看不到蓝。房间里,吸一口气,感觉都混着雨雾,被子褥子也避免不了。房间都已被雨雾打入内部。天潮地湿的,让人感觉即使在梦里,也处于一片迷雾。
有时雨会骤然而至。下午时分,从营地望去,一大片深蓝色的乌云正在不远处征战,除开它,天的别处都是一片宁静的蓝天白云,矿区也在晴朗之下。说时迟那时快,铁皮传来啪嗒啪嗒急促地响声,吹响着骤雨到来的号角。白天被炙烤了一天的大地,迎来一盆冷水澡。霎时间,空中扬起的尘土被雨雾拍打落地,空气被洗刷一新。黄色的大地上涌出了条条溪流,不管不顾地在大地的脸上划下数不清的或深或浅的沟壑。
矿区的车,不惧风雨,不停歇地工作。黄泥见不得车对雨的无视,借着雨给的助力,它们疯狂地溅到车窗车门上,又借着车辙转动,铆足劲要给车画上新的漆色。而雨,它只顾裹挟着空气中的尘土气,奔向远方,干脆利落。它匆匆离去,留下一个清凉的夜晚。铁锈味混着土腥气在空气中浮游,那是矿脉脏腑里发出的呼吸。
雨时而暴烈,常携狂风而至。夜晚时分,天空突然发怒,抬头一片暗黑,大雨像粗针一样落下,生灵避之不及。闪电如银蛇般撕裂天际,雷声如同战鼓,来自大自然的怒吼如在身旁,令人心悸。狂风暴雨之下,行进的矿车也得为它短暂地停歇,只能在雷声中如驯兽般低伏。不知名的各种飞虫奋力地闯进人们居住的房间作庇护所,它们向着有光的地方不知疲惫地撞去,在门前、在窗边、在灯旁,散落了一地的残骸。晨光扫去虫骸时,总有人想起昨夜又有多少“星光”,在灯罩上陨落。
矿山的雨,它是入骨的潮,是刮漆的刀,是悸心的鼓。在这片土地上,它拨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。矿山人的命脉,早已在雨中,被浇铸成了矿脉的形状。